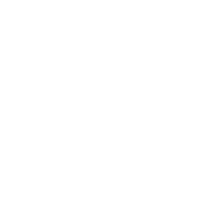苦雨經(jīng)風(fēng)也解晴 ——印象詹仲堃
作者:蔣嘯虎
1990年底,詹仲堃與世長辭,參加追悼會的有“省花”曾與他共事的同志和“省藝校”的師生們,我被指定作為他的生前好友致詞。我凝視他的遺容沉痛地說:“詹仲堃走了!帶著他對人生的迷茫和無奈,悄無聲息地走了!他在臨終前,曾拉著我的手說蔣嘯虎啊!我并不怕死,我是不甘心!我活了七十一歲,而讓我工作的時間只有一十七年!我不甘心啊!!!……”講到這里,我已泣不成聲,會場上亦一片唏噓,“不甘心”這三個字蘊藏了多少潛臺詞啊!在回程的車上,余譜成紅著眼睛對我說:“他還導(dǎo)演過《梁山伯與祝英臺》呢!”時任“省藝校”教務(wù)處主任的周宏頤更為嘆息:“如果能讓他多工作二十年就好了!”天妒英才啊,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不過有這么多人為之惋惜,也算為他凄風(fēng)苦雨的一生,畫上了一個雖不完美、卻能告慰在天之靈的句號了。
詹仲堃畢業(yè)于新中國成立前的國立劇專(“中戲”的前身,已承認(rèn)其學(xué)歷),1950年參加湘江文工團(tuán),演技很出色。比如在《雙送糧》劇中所扮演的老農(nóng),其水平至今無人超過;在歌劇《消滅侵略者》中飾演機(jī)槍手,導(dǎo)演高林贊嘆說,“只有他才像志愿軍戰(zhàn)士”。“省花”建團(tuán)后,他成為“十八羅漢”之一。在省戲曲會演中導(dǎo)演了《中秋之夜》,本來劇中父親一角由胡雍林扮演,后因誤被隔離審查,匆忙間要他頂上,卻為該劇添色不少,獲得演員二等獎。還曾與我向何冬保老師學(xué)了《小砍樵》,照本宣科地演出后,他對我說,“出場的臺步要改,不像是上山,而是出操。”于是改為在深山茅草中行走的步子;還有對于捆柴的過程他也發(fā)現(xiàn)了問題,認(rèn)為何冬保老師那是藤條,而后來的表演卻是破竹;藤是不須剖開的,只要用腳踩住一頭,然后用雙手抓住另外一頭來擰,這才符合生活。可見他觀察入微。在赴朝期間,他說,《砍樵》中劉海唱著,“將身且把山林進(jìn)”,轉(zhuǎn)身那一跳姿態(tài)不好看,問我會不會“旋子”,我說曾向桂希科老師學(xué)過,他就建議我改。后來我演的時候就是照他以上說的這些來做的。
至于導(dǎo)演這一行,他對我說過,當(dāng)導(dǎo)演是誤打誤撞碰上的。那是1950年冬,湘江文工團(tuán)參加土改時,深為翻身農(nóng)民踴躍送公糧的情景所感動,徐叔華說,“真想寫一個戲來反映這種激動人心的景象!”而他也心血來潮,把胸脯一拍,“你寫得出,我就排得出!”熟料徐叔華果真實發(fā)靈感,連夜寫出了劇本。當(dāng)高林把本子交到他手中時,一看就傻眼了,“這戲怎么導(dǎo)啊?!”要布景吧,場景轉(zhuǎn)換得太頻繁,又是山,又是平地,要上坡、下山,又要越坎過溝,還要你追我趕,總共不過十五分鐘的戲,就是電影蒙太奇的手法,也會令人眼花繚亂。何況劇本雖然寫得簡練,但卻充滿激情,要怎樣才能在人物的行動中得以體現(xiàn)?而土車子和籮筐,如果用真的,到時土車推不動,擔(dān)子挑不起,還得趕路,臺上不亂成一鍋粥!他回憶這些時曾對我說,當(dāng)時真是“想破了腦殼!”(注:1956年赴京匯報演出時,《戲劇報》編輯曾約他寫一篇有關(guān)《雙送糧》導(dǎo)演創(chuàng)作的稿子,他則推薦由我來執(zhí)筆,后來因“反右”運動而致流產(chǎn),如今簡約報道也算了卻宿愿)。想來想去,想到了看過的京劇《挑滑車》,思緒豁然開朗,既然“高寵”能以鞭代馬,能通過演員的表演,用槍來挑虛無一物的滑車,而在挑的過程中又用自身的形體動作來表現(xiàn)馬的疲憊;那么,也可以用車扁擔(dān)和纖繩來表現(xiàn)土車子,而又通過演員的表演來體現(xiàn)行進(jìn)的路況。接著,又到實際生活中去體驗。他說,“不學(xué)不知道,一學(xué)嚇一跳”。剛推土車子,空車還勉強(qiáng)能歪七歪八走幾步,而綁上了實物,一推還沒開步就車翻人倒。再仔細(xì)觀察、體會,一步一步地、總結(jié)出那句精辟的經(jīng)驗:“若要土車穩(wěn)又快,全靠屁股兩邊甩。”平衡不在于手,而是靠臂力來掌握的,這樣一來,整個導(dǎo)演構(gòu)思就呼之而出。
《雙送糧》是在牛欄里排出來的。他把纖繩的一端綁在欄柱上,要龔業(yè)珩去拉,行走、跨步、跳躍、轉(zhuǎn)彎,繩子都不能偏移,一遍又一遍,累得她腰酸背疼腳抽筋。龔業(yè)珩那時才十五歲,嘟著嘴埋怨說:“以后如果是你導(dǎo)演的戲,我再也不演了!”當(dāng)然,這不過是小孩賭氣的話,后來他倆還是合作得很好。當(dāng)1985年省電視臺對《雙送糧》的三位演員進(jìn)行現(xiàn)場采訪的直播中,那時龔業(yè)珩已經(jīng)49歲了,憶及當(dāng)年仍忍俊不禁。
有人說,這個戲是徐叔華成全了詹仲堃;而又有人說,是詹仲堃成全了徐叔華。依我看,兩種說法都對,但還應(yīng)該加上朱立奇(是他改編了《瀏陽河》,使之成為名曲),“知音偶一時,千載為欣欣。”是他們?nèi)说墓餐瑒?chuàng)造,才使得《雙送糧》成為傳世之作。
《雙送糧》劇照
他的思路很敏捷,不論是導(dǎo)演戲劇或在“省藝校”擔(dān)任表演教師時,都猶如天馬行空似的。比如,有一天,他翻閱我改編的《相思女子店》,看著其中借用的《我儂詞》念了起來:“我儂兩個,特煞情多!捏一個你,塑一個我。忽然歡喜呵,將它來打破,重新下水,再練再調(diào)和,再捏一個你,再塑一個我,那其間,那其間,我身子里有你,你身子里也有我。”他問道,“這是你寫的?”我說,“我哪有這種才華,我這是借古人的詞,抒人物之情。”他一拍腿站起來,興奮地說,“這不正好說明了演員與角色的關(guān)系嗎?我要把它再細(xì)化,編一本表演教材!”我這個引用者從來也沒從這方面去想過,而他卻敏銳地捕捉到了。
由于性格使然,他排戲從來是個“獨行俠”,不喜歡別人摻合。我看他構(gòu)思時,總是在夜深人靜時默默地思考,每一步驟、每一個細(xì)節(jié)都分析得很細(xì)密,然后才付諸實施。
他很傲,很倔。1978年,我在長沙街頭遇見他在擺地攤,賣書報雜志;見他仍然如此落魄,便拉著去吃飯,席間,他告訴我離開后不幸的遭遇。談起一件事,使我至今難忘:“文革”期間在某縣劇團(tuán)曾參加一次會議,結(jié)束時,大家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他也同樣舉起手大聲喊著。而一個造反派頭頭對他吼道,“你這個五 反分子,這個口號你也配喊?!”他反問,“我不喊毛主席萬歲喊什么?”那個造反派二話不說,狠狠地一拳打落了他四顆門牙,還吐了一口痰說,“我教你喊!”他說起這件事聲淚俱下,張著嘴把我看,“我現(xiàn)在連說話都不關(guān)風(fēng)了!”接著又說,“你想想看,當(dāng)時如果不舉手喊,不但照樣會挨打,只怕還會被扣個反革命分子帽子批斗!”真是無法無天,有理難辯。后來,我去找了湘劇團(tuán)的一位領(lǐng)導(dǎo),看是否可以接納他做導(dǎo)演工作。她聽后當(dāng)即應(yīng)諾,“就是那個《雙送糧》的導(dǎo)演?行,你帶他來看看。”我便領(lǐng)他去了,見他依舊是破衣爛衫,便說“你也不換一套干凈衣服”。他苦笑著“我哪來的錢啊!”這倒是我疏忽了。去后,那位領(lǐng)導(dǎo)一看,也不知道避諱,當(dāng)面就說,“你就是詹仲堃啊!怎么連牙齒也沒有了?……唉,我們是湘劇,隔行如隔山啊”。(她卻不知,早在1954年冬詹仲堃就為湘劇排過《不能走那條路》還指導(dǎo)過名老藝人徐紹清老師,當(dāng)時有與其在說戲時合演的照片,這次去時,他揣在兜里並未拿 出來。)他一聽此話,扭頭就走,咕噥著,“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這以后,梁器之聽說了他的情況,毫不猶豫,把他推薦進(jìn)了“省藝校”,這才使他有了安身立業(yè)之所。在“省藝校”他排了《欄車》,這是他繼《雙送糧》之后,又一經(jīng)典力作,被評為優(yōu)秀教學(xué)劇目,他本人也被評為優(yōu)秀教師,實至名歸。
1988年,“省藝校”評職稱,各色人物充分亮相,使盡各種手段,爾虞我詐,相互傾軋;正直人士徒嘆奈何,只好保持沉默。某人剽竊了詹仲堃的表演教材,評得二級,惹得他勃然大怒,上告到文化廳。為了平息此事,校方某負(fù)責(zé)人說,可以讓他“評退”,他詰問 ,“我還差兩年,憑什么要我退休?”后來那人又要他“病退”,他更反感,“我又沒病,為什么要病退?你咒我呀!”就這樣,他便與職稱無緣。(儲聲虹聽說后說,按理詹仲堃應(yīng)評一級。)然而,是真金才會發(fā)光,沙礫再怎樣也成不了珠玉,“蓋棺論定”,公道自在人心。上世紀(jì)五十年代錘煉出來的“十八羅漢”這個群體,不論何時、何地、何事,總是這么超然,剛正不阿,與世無爭。
緬懷往事,故人的音容笑貌常在眼前掠過,令人感傷不已,不禁想起了普希金的一首詩: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不要憂傷,不要著急;
憂郁的日子需要鎮(zhèn)靜,
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將會來臨。
心永遠(yuǎn)向往著未來;
現(xiàn)在卻常是憂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會過去;
而那過去了的,
將會成為親切的懷念。
地址:湖南省花鼓戲保護(hù)傳承中心 電話:0731-87654321 E-mail:hnshgx@163.com
版權(quán)所有:湖南省花鼓戲保護(hù)傳承中心 湘ICP備202301572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