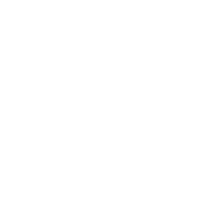自是花中第一流——記著名花鼓戲表演藝術(shù)家鐘宜淳
撰文/殷婷
這簡直就是一部傳奇!當(dāng)我一口氣讀完鐘宜淳老師親筆撰寫的自傳《一路笑著走來》,掩卷間無限向往和感慨。
那是怎樣一個豐富多彩的人生啊!八十五年的歲月,她見證了新舊社會的交替,在新中國波瀾壯闊的發(fā)展歷程中澎湃激揚;她見證了花鼓戲從“下三濫”的“淫戲”到扎根省城、走向全國、沖出國門,站在國際大舞臺上征服了全世界人們的光輝歷史;她從一個出身名門、世代書香的大家小姐歷經(jīng)風(fēng)雨成長為扎根民間、全心全意為人民大眾服務(wù)、德藝雙馨、家喻戶曉的花鼓戲表演藝術(shù)家。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不管歷史風(fēng)云怎樣變幻,她始終面帶微笑、不憂不懼、淡定從容,那顆熱愛花鼓、為花鼓而生、為花鼓癡迷的心永遠是那樣堅韌、年輕、充滿著激情。
“我的藝齡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歲。”說這話時,鐘宜淳老師慈祥的臉上洋溢著滿滿的幸福和自豪。
1949年,當(dāng)全國人民歡天喜地迎接新中國成立之際,在震天動地的鑼鼓聲中,時年20歲的鐘宜淳,也掀開了人生新的篇章,她順利考入了邵陽地委資江文工團,戴上了八角帽,著上了列寧服,系上了寬皮帶,穿上了橡膠鞋,成為了一名光榮的新文藝工作者!她夢寐以求的愿望終于實現(xiàn)了!
當(dāng)時的新文藝工作者,工作重心和任務(wù)就是密切配合黨的政策方針開展宣傳工作。回想慶祝解放,他們扭秧歌、打腰鼓、演《白毛女》《血淚仇》等歌劇的情景,85歲的鐘宜淳像孩子一樣歡快地笑出聲:“我們打腰鼓,從南門一直打到東門,圍觀群眾爭先恐后,兩邊街道擠滿黑壓壓的人群。一路之上,腰鼓聲、鞭炮聲、歡呼聲響徹云霄,整個邵陽城都沸騰了。”
這是年輕的鐘宜淳在生命中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人民群眾對共產(chǎn)黨的熱愛。黨群之間那種如魚水相連的親密關(guān)系,特別是《白毛女》的演出,激發(fā)出農(nóng)民反抗地主階級的覺悟。從現(xiàn)實中她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所說的:“文藝是消滅敵人、打擊敵人,教育人民、團結(jié)人民的有力武器。”她的心為之震撼,第一次認(rèn)識到了文藝的力量,她為自己能從事這樣有意義的工作而感到無限光榮。她決心要以一顆火熱的心服務(wù)人民大眾,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為新中國建設(shè)添磚加瓦。
1951年,黨中央號召新文藝工作者向傳統(tǒng)學(xué)習(xí),鐘宜淳便滿懷激情地向邵陽花鼓戲劇團學(xué)習(xí),并觀摩了花鼓戲《勸妻援朝》。這是她第一次真正地接觸花鼓戲。
在那個不算小的劇場,擠滿了前來看戲的人們,而且?guī)缀跞巧硐祰埂㈩^裹毛巾的勞動人民,座位兩旁還擺著扁擔(dān)箢箕。不難看出,他們剛結(jié)束一天的勞作,連家都沒顧得上回,連勞動工具都沒來得及放下,就迫不及待地趕到劇場看戲了。而當(dāng)大幕拉開,鐘宜淳很快就被劇情吸引。花鼓戲的唱詞是如此的通俗易懂,有腔有韻;演員的表演是那樣的生動,沒有絲毫裝腔作勢的舞臺腔,就像是生活中真實的人物。尤其是扮演妻子的顏如明居然是個年青小伙子,可他的一招一式竟比女演員還要逼真。鐘宜淳完全被他們的演技折服了。她頓時明白了,為什么勞動人民會這樣熱愛花鼓戲,因為花鼓戲親切易懂,貼近生活,最能被他們接受,能給他們帶來歡樂,能為他們消除疲勞。
散戲回來的路上,鐘宜淳仍陶醉在花鼓戲的巨大魅力中。她想,我國是農(nóng)業(yè)大國,擁有85%以上的農(nóng)民,勞動人民是這樣愛看花鼓戲,我要是能當(dāng)上一名花鼓戲演員,能擁有85%的觀眾那該是多么幸福!這個念頭頓時像一道耀眼的陽光,照亮了鐘宜淳的心,前方的道路豁然明亮起來。就這樣,她對花鼓戲從一見鐘情到陷入不可自拔。而上蒼似乎也聽到了她強烈的心聲和愿望,演花鼓戲的機會來了。
鐘宜淳參加勞動
1951年秋,全省文工團會演在省會長沙舉行。資江文工團決定學(xué)習(xí)邵陽花鼓戲劇團的花鼓戲《張謙參軍》,參加全省會演。鐘宜淳在戲里飾演張謙的娘。這是她第一次飾演老太婆。根本不知道怎樣舉手投足,完全是個典型的白坯子。可她下定了決心,不管怎樣,一定要把戲演好,于是,她找到了花鼓名藝人王佑生,虛心向他求教。佑師傅說,“演戲不是件容易的事,不是光憑扮相好,嗓子好,就能演好戲。要想把人物演活,就要做有心人。要仔仔細(xì)細(xì)觀察生活,觀察人物。要認(rèn)認(rèn)真真磨煉演技,一舉一動,一招一式都要記在心里。”
啟蒙老師王佑生的一席演出心得,讓鐘宜淳醍醐灌頂。從此,在長達六十多年的藝術(shù)生涯中,她始終牢記“有心人”這三個字。她找到了打開藝術(shù)之門的金鑰匙。在生活中,她處處留意、時時留心,無時無刻不在收集生活素材,吸收、消化、反芻、提煉、升華。
為演好老太婆,她深入生活,大量接觸并反復(fù)熟悉生活中遇到的各式各樣的老太婆,仔細(xì)觀察她們的言行,偷偷模仿她們的舉止,然后認(rèn)真思索、對比,最終挑選出適合劇中人物的動作,吸收借鑒到角色中。正是這種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藝術(shù)提煉,在演出當(dāng)日,鐘宜淳硬是將一個年過半百的老太婆演得活靈活現(xiàn)、血肉豐滿,博得觀眾如雷的掌聲和喝彩聲。該劇一舉奪魁,榮獲全省第一屆文工團會演一等獎,與湘江文藝團的《雙送糧》、工人文工團的《一件寶貝》并駕齊驅(qū),成為全省文工團匯演的三面鮮艷旗幟。
第一次學(xué)演花鼓戲就得此殊榮,鐘宜淳的心里充滿了欣慰和自豪,也從此更加堅定了要當(dāng)一名花鼓戲演員的決心。所以,當(dāng)1952年,適逢全省文工團整編時期,她竟金榜題名考取了中南大學(xué)(當(dāng)時稱礦冶學(xué)院)時,當(dāng)大家都慶賀她成為一名大學(xué)生有了錦繡前程時,鐘宜淳反而躊躇起來。面對擺在面前的兩條路,離開劇團上大學(xué)?還是放棄上大學(xué)當(dāng)演員?她徘徊著、反復(fù)思考著。最后,她做出了一個讓人們大跌眼鏡的決定——不當(dāng)大學(xué)生,要唱花鼓戲!
一石激起千層浪。她的這一豪言壯語引起大家議論紛紛。笑她傻,罵她糊涂,說她丟下金飯碗去撿討米棍,更是急壞了她那望女成鳳的母親,她母親說:“當(dāng)年,你七舅父為了看花鼓戲,氣得你外公挖了他一煙袋腦殼,出了不少血。你外公魏光燾是八省總督,他要是活著,知道你這個外孫女當(dāng)花鼓戲子會把你打扁。”哥哥姐姐也勸她“千萬莫錯失良機,走錯這一步,會后悔一世。”可鐘宜淳卻吃了稱砣鐵了心。她不顧家人和同事們的勸阻,豪情萬丈地在分配志愿表上重重地寫上“愿為花鼓戲事業(yè)奉獻終身”11個大字。當(dāng)她把分配表鄭重地交給組織時,只覺得心中陽光燦爛一片。
有舍必有得。命運為鐘宜淳準(zhǔn)備了一份厚禮。
湘江文工團和工人文工團合并成立了省文工團,鐘宜淳憑借出色的表演才華順利通過考試。進入了省里唯一的由新文藝工作者組成的劇團。
當(dāng)時的省文工團匯聚了全省的尖子文藝人才,既有著名的作曲家、歌唱家,也有她十分崇拜的名演員。在這樣一個人才濟濟的地方,每天都能接觸到許多新鮮的知識和事務(wù),這既是一種嚴(yán)峻的考驗,也是一次極好的鍛煉機會。天性樂觀、豁達的鐘宜淳如魚得水。對知識的渴望,對藝術(shù)修養(yǎng)的迫切需求,像源源不竭的動力,促使著她始終精神飽滿、干勁十足地游弋在藝術(shù)的海洋里。她接受了蘇聯(lián)著名導(dǎo)演列斯里的學(xué)生熊秉勛、宋紹文、張間等導(dǎo)演指導(dǎo)的大量的表演訓(xùn)練,系統(tǒng)地學(xué)習(xí)了國外先進的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體系。她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套先進的藝術(shù)理論,居然有許多地方與我們民間老藝人從生活中舞臺實踐中得出的表演經(jīng)驗吻合。原來,我們的民間藝術(shù),我們的傳統(tǒng)藝術(shù),是一朵真與美高度結(jié)合的奇妙之花,是一種獨特的表演體系,是一座礦藏豐富的寶庫。
為了向傳統(tǒng)學(xué)習(xí),鐘宜淳更加鉚足了勁,一頭扎進民間,孜孜以求,向名老藝人拜師學(xué)藝。得到了周斌秋、桂希科、王命生、王佑生、廖春山、唐三阿公、楊保生、楊福生、蔡教章等眾多名老藝人的指點,扎扎實實地學(xué)習(xí)了《討學(xué)錢》《放風(fēng)箏》《打鳥》《小藍橋》《小姑賢》等一系列經(jīng)典傳統(tǒng)劇目。為了唱出老藝人那極富花鼓韻味的腔調(diào),鐘宜淳無時無刻不在琢磨,一個調(diào)子反復(fù)練唱,上街散步唱,炒菜做飯唱,洗碗掃地唱,奶孩子也唱。而在學(xué)習(xí)表演時,鐘宜淳又極愛思考鉆研,十分好問,一個問題不打破沙鍋決不罷休。有次廖春山被追問急了,佯怒:“你挖傳統(tǒng),挖了我一雙眼睛,還想要擠出點水來啊!”
不瘋魔不成活。唱戲如癡的鐘宜淳就這樣扎根于廣闊的民間藝術(shù),如饑似渴地吸取著知識的營養(yǎng),她以令人驚訝的速度迅速成長起來,她的藝術(shù)理念和表演技能得到了質(zhì)的提升和飛躍,而這一切都是她用辛勤的汗水和心血一點一滴換來的。或許在某些人眼里,鐘宜淳哪天哪月都在流淌著“辛勞”二字,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累。然而在她的眼里,生活卻永遠是那樣的璀璨繽紛,每天有看不完的新鮮事,有學(xué)不完的知識,每天歌聲、琴聲、歡笑聲不絕于耳,渾身上下洋溢著一派勃勃生機。我想,這就是真愛了。因為真心地愛花鼓,所以不知苦,不覺累,無怨,無憂,也無悔。
鐘宜淳老師講述的那個年代,是十分令人著迷的。那時的人們物質(zhì)條件很艱苦,但精神生活卻十分富足;那時的人們,心思要單純得多,日子也純粹得多。在那個年代,處處洋溢著如火如荼的激情,人與人之間講求的是互幫互助、團結(jié)奮進。而火熱的生活、飽滿的激情,也為文藝創(chuàng)作帶來了源源不斷的靈感。作為演員,活躍在舞臺上的鐘宜淳,也時時被生活的激情沖蕩著。她第一次拿起了筆,澎湃的情感像放閘的湖水傾瀉筆端,她寫出了人生的第一個小戲——《姑嫂忙》。
鐘宜淳在《姑嫂忙》中飾演嫂嫂
這部借鑒邵陽花鼓戲《張古董打豆腐》的表現(xiàn)手法,反映姑嫂支援治湖的高尚情操,一經(jīng)面世就得到了領(lǐng)導(dǎo)的高度重視,迅速投入排練,而鐘宜淳成為了這個戲集編、導(dǎo)、演為一體的“全面能手”。在全省第一屆戲曲會演中,該戲榮獲五項獎:劇本一等獎、演出一等獎、導(dǎo)演獎、音樂演奏獎,以及她飾演“嫂嫂”一角獲得的“演員二等獎”。該劇本還相繼在《戲劇報》《洞庭工地報》發(fā)表,由湖南通俗讀物出版社的《新堤》出版,并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
“其實我是狗戴帽子碰中了。”談起人生的第一個劇本就獲得這樣大的榮譽,鐘宜淳坦承:“其實我從來沒有寫過劇本,是治湖的激情,是工作需要,激勵我拿起了筆。記得當(dāng)時湘劇老前輩彭菊生給我提了一個意見,他說我寫了一只香爐腳,說我最后結(jié)尾的唱只寫了三句,應(yīng)該是四句才對。你看,我連這個最基本的戲曲創(chuàng)作規(guī)律都不知道。我深感一個人在藝術(shù)上的成長是形勢逼出來的,是在實踐中逐步提高的,同時也是離不開眾人的智慧的。”(未完待續(xù))
《補鍋》電影版鐘宜淳老師唱段
1953年,省文工團分成話劇、歌舞、花鼓戲和管弦樂隊四個團。在《張謙參軍》中初露頭角,又在《姑嫂忙》中顯露編、導(dǎo)、演三面全能的鐘宜淳,無疑是進入花鼓劇團的絕佳人選。于是,領(lǐng)導(dǎo)毫不猶豫地將她分到花鼓劇團。同時一塊分來的,還有儲聲虹、張間、許在民、朱立奇、余譜成、梁器之、龔業(yè)珩、唐鏡明、譚亦之、銀漢光、蔣嘯虎、詹仲堃、周貴南、李石健、肖新初、曹香秋、歐陽振砥共18人。這支18人組成的花鼓演出隊就是省花鼓戲劇院的前身,業(yè)內(nèi)美譽他們?yōu)?ldquo;十八羅漢”。
這支“十八羅漢”組成的新型的花鼓演出隊為花鼓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后來又相繼吸收了有文化有知識的演職人員,他們用卓越的才華和見識,逐漸形成了省花鼓戲劇院的演出風(fēng)格,并指引帶領(lǐng)了當(dāng)時的演出風(fēng)尚。他們深厚的創(chuàng)作實力和文化底蘊,對省花鼓戲劇院的命運起到了十分關(guān)鍵的作用。“我們這個團不同于由藝人組成的花鼓戲劇團。”鐘宜淳侃侃道來:“解放前,花鼓戲是勞動人民自己創(chuàng)作的劇種,反映的大多是勞動人民自己的故事,解放后,花鼓戲從農(nóng)村走向了城市。只有創(chuàng)造表現(xiàn)當(dāng)前人民生活、斗爭的現(xiàn)代戲曲,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而我們團更是創(chuàng)作改編現(xiàn)代戲的先驅(qū),在現(xiàn)代戲的創(chuàng)作演出上我們是全省的一面鮮艷旗幟。”
從1957年誕生于農(nóng)業(yè)合作化高潮時期的花鼓戲《三里灣》(是許在民根據(jù)著名作家趙樹理的同名小說改編),到農(nóng)業(yè)機械化時期的《野鴨州》,再到后來《補鍋》的如日中天,鐘宜淳見證著每一部戲的成長。它們就像是她的孩子,她為之傾注了滿腔的熱情,付出了全部的心血。
在花鼓戲《三里灣》中,她飾演“常有理”,將一個蠻橫不講道理的婦人刻畫得栩栩如生,給觀眾留下了極深的印象。這個戲成為了省花鼓戲劇院演現(xiàn)代戲的一個新的里程碑。全劇充滿了濃郁的喜劇色彩,觀眾說看《三里灣》就像進入笑的天堂。當(dāng)時演員們一天三場的連著演,忙得不曉得白天還是黑夜,但就算這樣加班加點演出,還是不能滿足觀眾的需求。1958年,廣受好評的花鼓戲《三里灣》參加了全國現(xiàn)代戲調(diào)演,當(dāng)時,劇院被文化部評為全國編演現(xiàn)代戲的八大樣板劇團之一。
而花鼓小戲《補鍋》則是給鐘宜淳帶來最多喜悅和幸福的戲。在劇中她飾演“劉大娘”。演老太婆,鐘宜淳不是初次,在《張謙參軍》中她就成功扮演了張謙娘。但千人千面,不愿意重復(fù)自己的鐘宜淳,立志要演出一個不同的劉大娘來。為從生活中找人物原型,她深入農(nóng)村,在軍山體驗生活,她觀察住戶吳大娘是如何喂豬的,從而開啟了攪潲、數(shù)豬、喂豬、趕豬、抱豬那一系列來自生活的動作,將一個劇本中的劉大娘活靈活現(xiàn)地呈現(xiàn)在舞臺上。面對眾人的贊譽,鐘宜淳卻說,其實她只是個采礦者。只要演員隨時隨地從生活中采擷閃光的礦石,再提煉加工,就能讓角色達到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藝術(shù)完美呈現(xiàn)。
《補鍋》鐘宜淳飾演劉大娘
鐘宜淳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這個“有心人”時刻不忘在生活中采擷閃亮的礦石。看書讀報見著精彩的句子,趕緊摘錄下來;聚會聊天聽到生動的語言,馬上記到本上。文人學(xué)士的吟詩作詞、下市井里巷的俚語俗話、論壇網(wǎng)友的逗霸調(diào)侃,以及唐詩宋詞,各類風(fēng)格,各種口味,應(yīng)有盡有。看到她密密麻麻工整娟秀的字跡和摞起厚厚的手抄本,我真為她的敬業(yè)精神而感動。鐘宜淳就是這樣,饑渴地、永不滿足地收集、吸取著生活的營養(yǎng)。對于她來講,不僅學(xué)校是課堂,生活更是一座蘊藏豐富的大課堂,只要有心,處處可以學(xué),時時可以學(xué)。向生活學(xué)習(xí),沒有終點,永不結(jié)業(yè)。
1965年,《補鍋》參加中南地區(qū)文藝會演,被評為“全國上山下鄉(xiāng)巡回演出優(yōu)秀劇目”,由珠江電影制片廠拍成彩色電影。在全國放映,名噪一時。從此,銅鑼打響長城內(nèi)外,補鍋補遍大江南北。“在上海、南京、北京、杭州、武漢各大城市演出時,場場爆滿,盛況空間。劇場門口,每晚都擠滿了等富余票的觀眾。我們每到一處均受到當(dāng)?shù)仡I(lǐng)導(dǎo)的隆重接待。各地市縣的劇團都從四面八方趕來學(xué)這兩出戲,排練廳里常常是幾十百把個蔡九哥和林十娘,幾十百把個蘭英、小聰和劉大娘在學(xué)戲,連京劇表演藝術(shù)家袁世海也來學(xué)演蔡九,那種火紅的場景,可謂空前。”鐘宜淳說到這,無限感慨:“那時候的花鼓戲波及全國,遍地開花。除了劇本好、演員演得好,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得益于領(lǐng)導(dǎo)對花鼓戲的重視和關(guān)心。省委書記周小舟為《兩個黨員》寫前言,省委書記張平化親自為《牛多喜坐轎》的牛多喜定成分,宣傳部佟部長和戈部長三天兩頭來排練廳抓質(zhì)量,文化局局長胡青波、胡代煒、蔣燕、鐵可等,經(jīng)常親臨現(xiàn)場出謀劃策,聽我們對詞、聽我們練唱。領(lǐng)導(dǎo)們對每一個動作和臺詞提出他們的看法和意見,他們沒有命令式的家長作風(fēng),而是平起平坐的朋友式的琢磨商量。那真是一個充滿著團結(jié)友愛、干群合作、共同創(chuàng)造、甘苦共嘗的快活歲月。”鐘老師的聲音漸漸地越來越輕,嘴角帶著一絲笑容,望著遠方,而我也陷入了那段美好的歲月。就這樣,我們沉默了一小會,為了那曾經(jīng)的美好。她經(jīng)歷過的,而我夢寐以求的。
《補鍋》電影版劇照
回顧64年的藝術(shù)人生,100多個角色,鐘宜淳扮演的大多是二旦、彩旦和婆旦。她演的第一個花鼓戲《張謙參軍》,扮演的是個老大娘。這個戲成功了,卻也給她在表演上定了位。雖然以她的能力完全可以勝任別的角色,但從此再也難以走出演老太婆的軌道。而在所有的大戲里,以婆旦為主角的戲是極少的,可哪一個演員不希望站在舞臺的中央,作為主角接受觀眾目光的聚焦和洗禮呢?哪一個演員不希望擁有一部眾星捧月般的戲,在藝術(shù)舞臺上留下自己永難磨滅的光輝形象呢?“眼見青春流逝,而一些適合我的角色卻輪不到我來演,我心里確實不是滋味。”鐘宜淳坦言,“這是人之常情。可我只會短暫地,無聲地,在內(nèi)心進行自我斗爭。我常以‘只有小演員,沒有小角色’‘愛心中的藝術(shù),不愛藝術(shù)中的自我’來要求自己,所以我會很快地將個人得失置之度外,而盡力地將我的每一個角色演好。戲曲是綜合性的藝術(shù),幕后有很多英雄,如燈、服、導(dǎo)、效和樂隊等,他們奉獻得還少嗎?有的甚至一輩子默默無聞。基于這種思想,我釋去了心上的重負(fù),從而愉悅地投入角色的創(chuàng)作中去。”
正是因為這種熱愛藝術(shù)、不計名利得失的態(tài)度,鐘宜淳始終心胸坦蕩,淡定從容。每接一個戲,無論飾演什么角色,無論戲份重輕,均是食之如飴,認(rèn)真對待。《補鍋》中的劉大娘、《姑嫂忙》中的嫂嫂、《小姑賢》中的惡婆婆、《討學(xué)錢》中的陳大嫂、《牛多喜坐轎》中的柳葉嫂、《謝瑤環(huán)》中的武則天、《柯山紅日》中的咖咯呷、《碧螺情》中的禿二嬸、《送表妹》中的姑媽等等,個個活靈活現(xiàn)、精彩紛呈,在戲曲舞臺上留下了濃墨重彩、令人難忘的一筆。著名音樂編配左希賓老師夸獎她,“不管什么角色,只要到了鐘宜淳手里,她是從不放松的,一句唱腔,一句臺詞都沒有一點浪費,沒一點糟蹋,她總是將角色刻畫得淋漓盡致。” 1983年,她在赴美演出的《劉海砍樵》中成功飾演“劉母”一角,獲得這樣的評價:“劉母的扮演者鐘宜淳,早在1955年湖南省戲曲會演中獲演員獎,擅長扮演二旦、老旦和現(xiàn)代中年婦女。做功細(xì)膩,表演人物性格鮮明,唱腔字正腔圓,富于花鼓戲特色,深受觀眾稱道……”
《南海長城》鐘宜淳飾演阿螺
《三里灣》鐘宜淳飾演常有理
《英雄列車》鐘宜淳飾演列車長
《柯山紅日》鐘宜淳飾演咖洛呷
《謝瑤環(huán)》鐘宜淳飾演武則天
她是一個難得的多面手。作為演員,在舞臺上忙著塑造千人千面的人物,足跡走遍三湘四水,演遍大江南北。她把花鼓戲送到工廠農(nóng)村、部隊礦山、機關(guān)學(xué)校、異國他鄉(xiāng),甚至是朝鮮戰(zhàn)場和對越南自衛(wèi)反擊前線。同時,她又作為編劇,辛勤耕耘跋涉在基層、劇壇。白天練完早功,晚上加班點燈熬油寫劇本。一邊隨團演出,一邊擠業(yè)余時間寫作,超負(fù)荷地忙碌于兩者之間卻不知疲倦。
我很難想象,一個女子,是要有多么強健的體魄和堅強的意志,是一種怎樣的決心和信仰,才能支撐著她這樣不怕艱辛、無畏無懼地一路走來。面對生活和困難,始終樂觀從容,用陽光般的笑容和信心,影響帶動著身邊的同事和朋友,創(chuàng)造了一次又一次的藝術(shù)輝煌。
對此,鐘宜淳說,“因為我始終牢記服務(wù)人民大眾,我忠于我的觀眾。”正是基于這種為人民服務(wù)的思想,1975年,當(dāng)鐘宜淳被任命為編導(dǎo)組組長,領(lǐng)導(dǎo)要求她全心全意專職“筆桿子”時,她最終選擇了服從。“其實我根本不想搖筆桿子。”鐘宜淳說,“雖然1952年創(chuàng)作了處女作《姑嫂忙》《四姐妹夸夫》,繼而又與人合作寫了《還牛》《兩個黨員》《年青一代》《救救她》等劇本,顯露了我在編、導(dǎo)上的才能。但我心里最喜歡的還是唱唱跳跳。只要大筒一拉就喉嚨發(fā)癢,只要看到舞臺就渾身來勁。當(dāng)看到一個個被觀眾喜愛的角色被別人替代時,心里真不是滋味。”那份對舞臺的眷戀之情,讓她柔腸百結(jié)。然而她追求的是心靈的凈美和人品的完善,雖然非常渴望舞臺,但總覺得自己不應(yīng)該選擇工作,只能讓工作來選擇自己,個人必須舍棄愛好來無條件地服從組織的分配。于是,她不再心有他念,而是全身心地和陳蕪、徐叔華、彭復(fù)光、湯師堯投入到大型現(xiàn)代戲《野鴨洲》的創(chuàng)作中。
為寫好劇本,他們五人多次到省農(nóng)機局采訪,先后跑了湘潭、株洲、安鄉(xiāng)等七個縣,深入華閣、安仁、安武等17個農(nóng)機站。“生活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chuàng)作源泉。那段時間,我的心常隨著時代的脈搏跳躍,每天聽到的想到的很多很多,我深感一出戲的好壞深淺是生活決定的,編造的東西不管多么華麗,都是平面枯燥的。只有生活才會讓作品注入生命。”
一年的辛勤努力終于換來豐碩的果實。1976年《野鴨洲》首演,得到了當(dāng)時省委書記張平化的肯定,并為全省農(nóng)業(yè)學(xué)大寨五千多代表演出,引起極大的轟動。1977年,在工農(nóng)兵座談會上,給了此戲很高的評價:“《野鴨洲》是一顆閃光的衛(wèi)星,是一枚重型炮彈,是一盤清新的鮮菜,擺脫了一整套的說教,有濃烈的生活氣息……”1978年,該劇本在《人民戲劇》上發(fā)表,1981年由珠江電影制片廠拍成電影。(未完待續(xù))
《小姑賢》鐘宜淳老師飾演姚氏
日子就這樣在快樂和充實中一天天過去。鐘宜淳,這個心無旁騖的花鼓信徒,在1990年,辦完了退休手續(xù)。然而,卻仍是退而不休,始終情系花鼓,心戀花鼓。在舞臺演出、電視熒屏、大學(xué)講壇、縣市劇團、業(yè)余輔導(dǎo)等場所,經(jīng)常可以看見她活躍的身影和爽朗的笑聲。就像當(dāng)年她說的那樣,她是要為花鼓事業(yè)奉獻終生的。
剛退休的前幾年,因為《補鍋》的劉大娘、《討學(xué)錢》的陳大嫂、《小姑賢》的姚氏尚未有人接班,于是鐘宜淳常被院里叫去演出。別人認(rèn)為辛苦的事,對鐘宜淳來說卻是求之不得。她認(rèn)為世上最快活的事莫過于唱戲過癮。所以,當(dāng)全省掀起錄制花鼓戲磁帶的熱潮,幾家音像社爭先恐后搶她去錄花鼓戲磁帶時,她更是滿心歡喜,欣然應(yīng)允。不僅以一己之力,沒日沒夜地挑選劇本,修改唱段,又編又導(dǎo)又演,還三天兩頭擠公交,來回奔返于老廣播電視廳和家里。為了錄上一盤磁帶,有時從早到晚,整整錄上十個小時,嗓子都唱啞了,也仍然開心。雖然一盤磁帶只有區(qū)區(qū)200元勞務(wù)費,少得可憐。可她卻說:“能為花鼓戲留下珍貴的資料,能為花鼓戲愛好者送去歡樂,就是我最開心的事。你想想,那些花鼓老前輩們,他們沒能趕上今天的好時代,他們唱得那樣好,卻未曾留下任何影像資料,這是花鼓戲藝術(shù)寶庫的重大損失。我跟他們比起來,那簡直是太幸福了。”
錄音棚的日子,成為了鐘宜淳藝術(shù)人生中又一個值得回味的珍貴記憶。她先后共錄制了《湘子化齋》《秋江赴潘》《張古董打豆腐》《張二嫂回娘家》《送表妹》等37盒花鼓戲磁帶。一時間,湖南的農(nóng)村城鎮(zhèn)、街道巷尾、茶樓酒館,都飄散著濃烈的花鼓戲韻味。鐘宜淳走在街上,駐足留連,傾聽著自己的演唱,那種巨大的快樂、滿足和成就感,自然是黃金萬兩也無法給予的。
花鼓早已成為她生命中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她是如此的愛著花鼓,她認(rèn)為,只要哪里有觀眾,哪里就是舞臺。于是,當(dāng)長沙的娛樂事業(yè)迅猛發(fā)展,各式夜總會和歌廳遍布城市各地時,鐘宜淳攜帶著方言小品來了,同時,她把花鼓戲帶進夜總會,帶進歌舞廳。她先后寫了《新編小姑賢》《嫁娘》《傻女》《學(xué)藝》等小品。語言生動幽默,人物個性鮮明,演出得到了觀眾的認(rèn)可,他們大聲喊著“歡迎劉大娘唱一段花鼓戲!”。這時,鐘宜淳便會喜笑顏開、飽含激情地為他們演唱《劉大娘笑呵呵》等經(jīng)典唱段。同時和觀眾一起高唱《劉海砍樵》里的“比古調(diào)”,她看到了花鼓戲旺盛的生命力,她為花鼓戲依然擁有這么多觀眾而興奮激動。
鐘宜淳老師和龔谷音老師表演小品
當(dāng)電視臺辦起《聚藝堂》《十九和弦戲樂匯》《戲曲嘉年華》等欄目和活動時,為宣傳花鼓戲,擴大花鼓戲影響力,鐘宜淳更是義無反顧、不計報酬、不知疲憊地參與其間,傳授知識、登臺獻藝、點評賽事,她將全部的心力傾注于她終愛一生的花鼓事業(yè),一顆火熱的心隨著歡騰的人群和熟悉的花鼓曲調(diào)跳動著激蕩著。而戲迷們的激情、執(zhí)著、癡迷也時時撞擊著她的心靈,每天電話鈴聲、書信,頻頻而至。戲迷們熱情的問候和發(fā)自內(nèi)心的喜愛,更是讓鐘宜淳感動不已。她為臺上花鼓戲后繼有人而由衷地欣慰,她為臺下花鼓戲仍有這么多鐵桿粉絲而驕傲自豪。她堅信,不管時代怎樣變遷,花鼓絕不會滅亡,永不會落幕!因為,越是地方的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越是國際的。花鼓一定會迎來百花齊放的春天!
退休后的鐘宜淳,反而比以前更加忙碌了。她抓住每分每秒,她珍惜每分每秒。她認(rèn)為,藝術(shù)是生命,生命是藝術(shù),而勤奮可以延長和開拓生命藝術(shù)。她練書法、學(xué)繪畫、寫打油詩、學(xué)英語。每天都安排得滿滿的,每天都過得有滋有味、興致盎然。
許多人都喜歡她寫的打油詩,她的打油詩通俗易懂,瑯瑯上口,不僅生動,而且親切有味。她不僅用打油詩編寫短信,發(fā)節(jié)日祝福,與人交談。還用打油詩寫日記,記載生活中的所遇所思所想。當(dāng)問起她,為什么迷上寫打油詩時,她說:“下里巴人愛打油,四六句子順口溜,鄉(xiāng)土俚語花鼓戲,練就筆墨寫春秋。因為我是一名花鼓演員,我這輩子始終忠實于我的觀眾。花鼓戲的觀眾是勞動人民,他們喜歡打油詩那樣平實生動的語言,所以我就要寫那樣的語言。”
關(guān)于民間語言,飽讀詩書的鐘宜淳有自己的看法。她不止一次地在大學(xué)講壇,語重心長地告訴莘莘學(xué)子,切莫看輕了我們的民間藝術(shù)和勞動人民的語言。這些看似樸實無比的話,往往極其生動,蘊含著深刻的哲理。一個人要講富麗堂皇的話很容易,要寫那些風(fēng)花雪月的詞也簡單,難就難在,用最普通無華的字眼,生動、精確而又極富意味地表訴人類的情感。鐘宜淳認(rèn)為,這樣的語言,才是雋永的語言,是花鼓的語言。這也是她如此堅持筆耕不輟、熱愛打油詩的原因。
2013年10月,湖南省花鼓戲劇院喜迎建院六十華誕。為創(chuàng)作好反映省花六十年風(fēng)雨歷程的紀(jì)錄劇《亮相》,鐘宜淳更是不顧84歲高齡,多次出謀劃策,指點并幫助主創(chuàng)人員進行藝術(shù)創(chuàng)作。并于院慶當(dāng)日,滿腔激情地再次登上舞臺,她要在這個特殊的日子里為自己終愛一生的花鼓戲,為之奮斗終生的花鼓戲,一展歌喉。當(dāng)一曲充滿濃烈花鼓韻味的“劉大娘笑呵呵”唱罷,現(xiàn)場的觀眾沸騰了,掌聲、喝彩聲、吶喊聲,在劇院上空久久回蕩。演出結(jié)束后,感慨萬千的鐘宜淳心潮翻涌,于是,她以充滿感情的筆觸,一氣呵成,揮毫寫下了長達56句的“打油詩”——《花鼓六十華誕有感》:
“花鼓華誕六十秋,十代同堂笑語稠。
新老藝友歡聚首,萬般感慨涌心頭。
曾記當(dāng)年風(fēng)華茂,投身藝海壯志酬。
金榜題名非我愿,甘當(dāng)花鼓一頑囚。
頂風(fēng)冒雪洞庭走,送糧推磨放歌喉。
赴朝慰問志愿軍,有求必應(yīng)戰(zhàn)不休。
晉京獻演三里灣,踏笑金坡上高樓。
銅鑼鐵鍋錚錚響,中南會演展風(fēng)流。
多喜老倌三易轎,拜壽哭爹笑不休。
野鴨洲畔頌機手,風(fēng)波迭起鬧湖洲。
劉海九妹飛海外,好評如潮震神州。
桃花涌汛花兒秀,梅花傲雪占鰲頭。
老表殊榮奪魁首,登峰造極躍飛舟。
好戲連臺數(shù)不盡,芝麻開花勝舊籌。
六十春秋勤戰(zhàn)斗,同舟共濟不言愁。
肩挑背荷基層走,三湘四海足跡留。
為工為農(nóng)為大眾,耕耘澆灌汗水流。
謳歌社會謳歌黨,旗幟鮮明唱沉浮。
尊師敬長迷傳統(tǒng),博采眾長勤交流。
致力傳承又啟后,創(chuàng)新改革爭上游。
換來花開葉繁茂,碩果累累滿枝頭。
花鼓情結(jié)剪不斷,夢里猶在藝中游。
痛泣連年失戰(zhàn)友,功勞業(yè)績?nèi)f代留
眼看夕陽桑榆晚,同齡個個皆白頭。
喜的后浪推前浪,后繼有人樂無憂。
湖湘文化鐵鑄就,鄉(xiāng)土魅力情悠悠。
千變?nèi)f化根牢系,緊把人民記心頭。
祝愿花鼓添錦繡,再創(chuàng)輝煌寫春秋。”
全詩高度概括了省花六十年的風(fēng)雨歷程和取得的藝術(shù)成就,寄托了自己對花鼓事業(yè)的無限熱愛和衷心祝福。
文化部部長雒樹剛對86歲高齡登臺的藝術(shù)家豎起了大拇指
往事,并不如煙。回首這漫漫的64年,鐘宜淳創(chuàng)作并與人合作的大小劇本40余個;錄制花鼓戲磁帶35盒;除處女作《姑嫂忙》外,導(dǎo)演的《三郎相親》榮獲湖南省“洞庭之秋”演出一等獎,導(dǎo)演并主演的《嘻隊長與滿堂客》戲曲廣播劇獲全國省、市優(yōu)秀節(jié)目評比一等獎;1979年她擔(dān)任全國第四屆文代會代表,并當(dāng)選為全國劇協(xié)理事;2008年她榮獲全國劇協(xié)頒發(fā)的“哺育新梅獎”;2009年榮獲中國文聯(lián)頒發(fā)的“從事新中國文藝工作六十周年的榮譽證書”和獎?wù)?2011年榮獲中國現(xiàn)代戲研究會頒發(fā)的“中國戲曲現(xiàn)代戲榮譽獎”;《湖南戲劇》曾載文評價:“她戲路寬,尤以演喜劇見長,表演生動,富于情味,唱腔臺詞清晰入耳,音色明亮,韻味足。”《湖南廣播電視報》評價:“她能編、能導(dǎo)、能演,是藝術(shù)上比較全面的多面手。”美國《華府新聞報》評價:“鐘宜淳扮演劉海的母親,能編、能導(dǎo)、能演,是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的理事,曾在兩部花鼓戲藝術(shù)片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她親自撰寫出版的著作《一路笑著走來》,著名作家譚談為書作序,稱贊“這是一部啟迪人生的書,是一部傳承藝術(shù)的書。這是一部留給文藝界、留給社會、留給后人的厚重禮物”。
我想,如果要從百花中選出一朵比作鐘宜淳老師,那不是牡丹,雖然她的藝術(shù)人生和成就像牡丹那樣濃麗絢爛,但她沒有牡丹身居廟堂為富貴綻放的盛氣;她也不是荷花,雖然她的藝術(shù)理想和人生品質(zhì)的追求就像出淤泥不染的荷花一樣純潔無瑕,可她沒有遠離人群獨居幽池的孤芳自賞;她也不是菊花,雖然她像菊花一樣傲骨挺立無懼歲月的風(fēng)劍霜刀,但她的芬芳和甜美不僅僅只在一年的一個季節(jié)里燦爛怒放。她應(yīng)該是外表淳樸平實但內(nèi)心蕙質(zhì)聰穎,她不事張揚但靜吐馨香;她年復(fù)一年日復(fù)一日地默默扎根廣闊的土壤,無論陰晴圓缺,不分春秋冬夏,讓每一個走近的人都如沐春風(fēng)、清香滿懷。是的,她就是那樸實無華卻芬芳馥郁的四季桂,既有鮮花的嬌美也有喬木的堅挺。“梅定妒,菊應(yīng)羞,”“何須淺碧深紅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完)
《打鳥》片段鐘宜淳老師飾演宋氏
地址:湖南省花鼓戲保護傳承中心 電話:0731-87654321 E-mail:hnshgx@163.com
版權(quán)所有:湖南省花鼓戲保護傳承中心 湘ICP備2023015723號